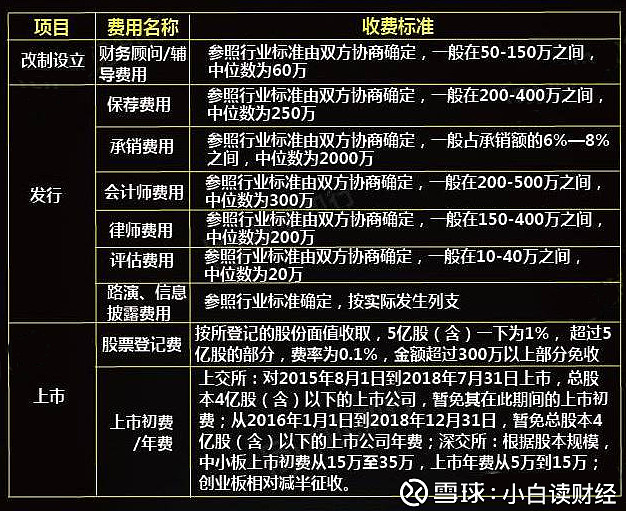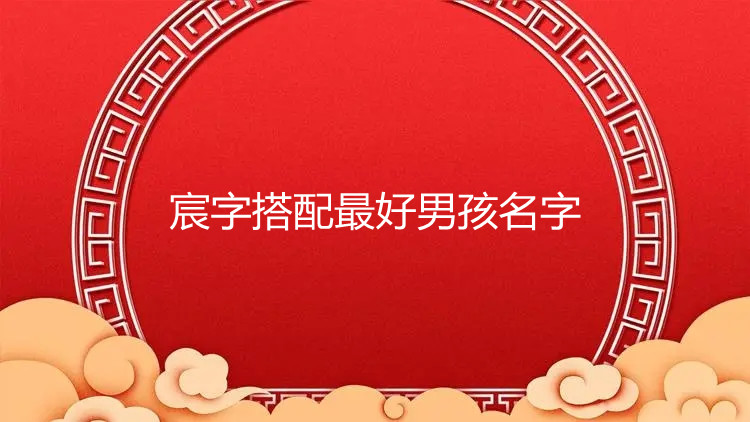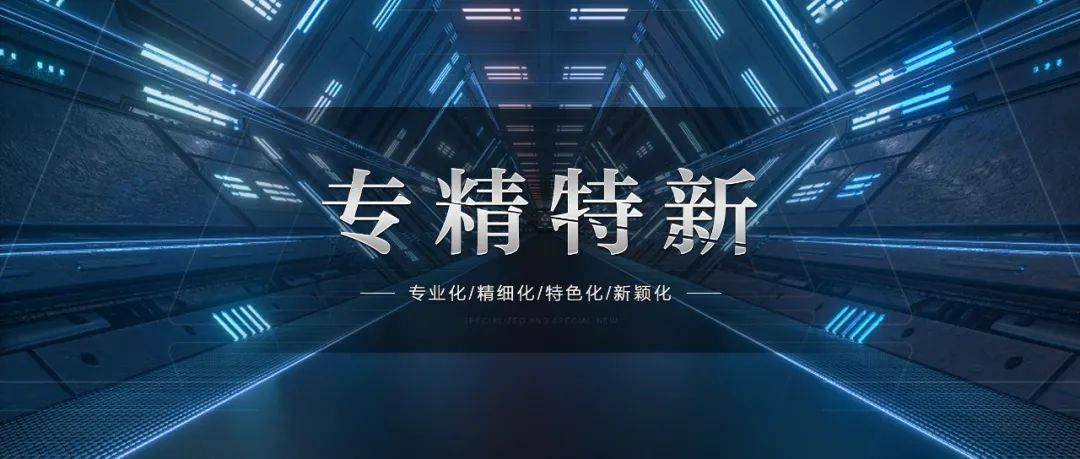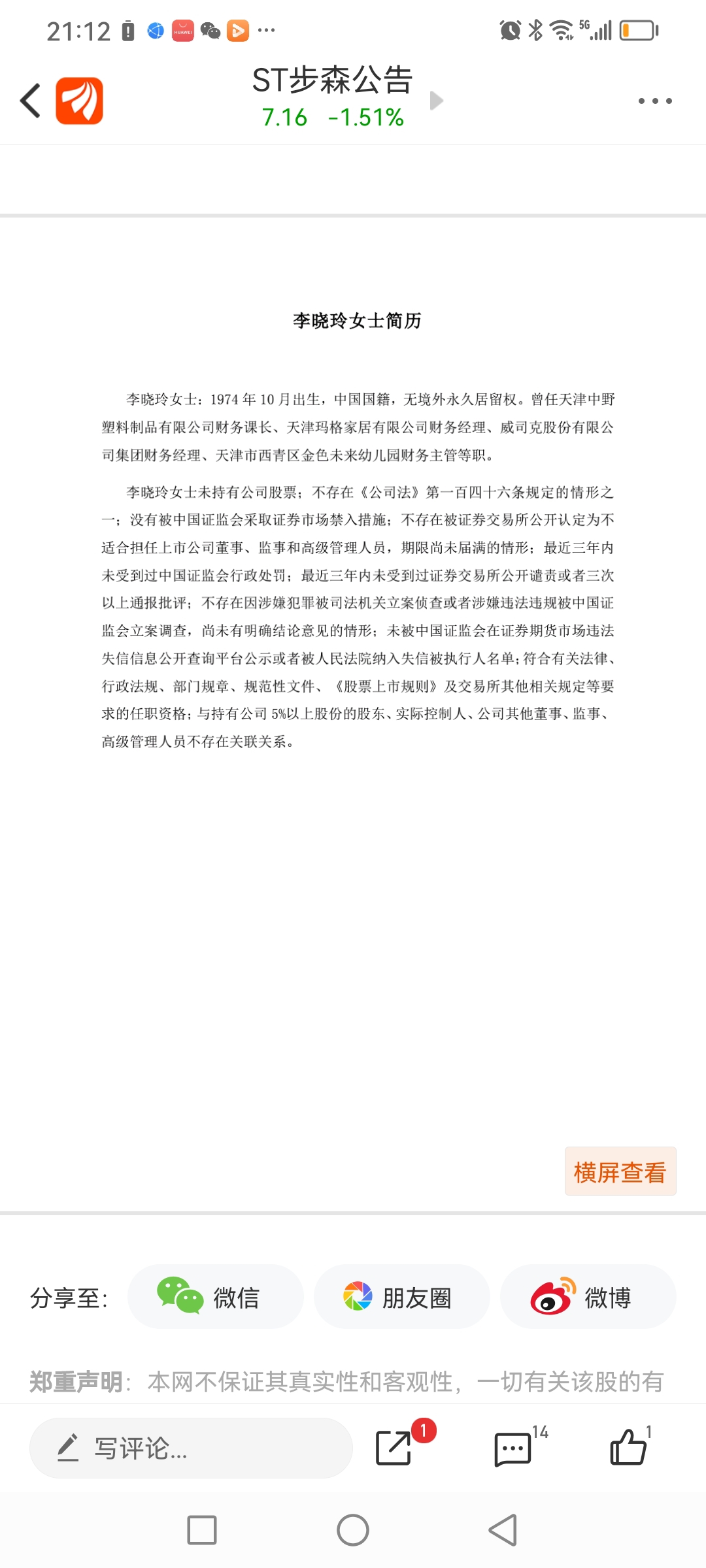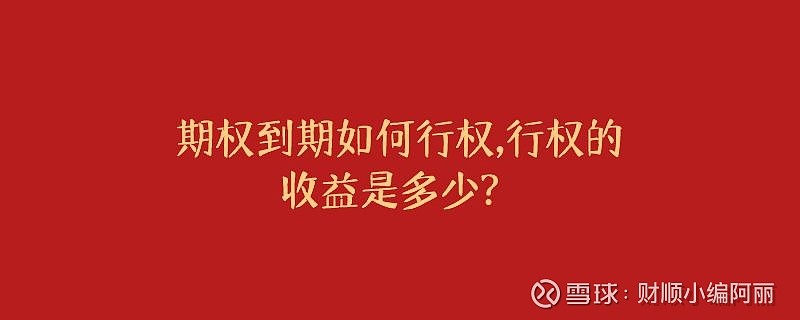出品|开源中国近年来,众多国内互联网大厂纷纷设立开源办公室(OSPO),其中部分企业在OSPO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然而,OSPO这一概念往往被外界误解,甚至被视为一种形式上的存在,被质疑其价值与资源投入是否合理。
为此,本文特别邀请了四位行业专家,共同探讨真实的OSPO究竟是怎样的。
主持人:王晔倞(头哥),支流科技技术VP、Apache APISIX Committer观察员:tison,公众号“夜天之书”作者、Apache Member & 孵化器导师分享嘉宾:Keith Chan,CNCF中国区总监、LF亚太区策略总监;堵俊平,华为计算开源业务(OSDT)总经理、LF AI & DATA基金会主席;边思康,蚂蚁集团技术战略发展部资深专家、开源办公室执行负责人。
话题 1:OSPO是怎样的存在?主持人王晔倞(头哥):什么是OSPO?它有哪些形式?请观察员tison来谈谈。
tison:OSPO,全称为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,中文翻译为开源办公室。
从企业应用案例来看,这个名字贴切描述了OSPO的职能。
OSPO的本质在于解决企业在使用、参与和发起开源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随着软件成为商业活动的核心,几乎所有的业务都依赖软件,而软件通常包含开源组件。
因此,企业无论大小都会参与到开源活动中。
OSPO的成立旨在解决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合规、安全、研发、市场和运营等多方面问题。
在企业架构层面,OSPO的形态多样。
在中国,常见的形式是虚拟组织,其职责侧重于法务、安全、研发等,与市场、运营部门有一定联系。
对于开源技术创业公司,OSPO往往作为整体市场策略的一部分,与市场部门紧密挂钩。
而实体部门则可能直接向CEO汇报,或挂靠研发部门,由CTO或技术VP管理。
话题 2:OSPO解决哪些问题?主持人王晔倞(头哥):企业如何通过OSPO解决实际问题?堵俊平:OSPO的设立源于企业在开源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挑战,如如何选择合适的开源软件、如何管理开源软件以支撑业务发展、如何合规使用开源软件等。
随着业务转型,特别是从传统产业向IT产业的转变,企业不仅使用开源软件,还通过贡献开源项目来构建产业生态和伙伴网络。
在此背景下,OSPO的职责扩展至构建开源战略,以服务业务战略和构建产业生态。
话题 3:OSPO面临的挑战主持人王晔倞(头哥):OSPO在运营中面临哪些难题?堵俊平:OSPO在虚拟组织和实体组织两种形态下面临的挑战不同。
虚拟组织可能无法高效响应业务需求,而实体组织则需要平衡作为COO、CMO、CTO和CEO的角色。
在开源环境下,OSPO需要面对的挑战包括:如何在开源社区中有效沟通、解决争议、建立合作关系、进行宣传推广,以及处理与市场部门的协调关系。
同时,OSPO还需要解决合规性问题、安全风险和对外交流问题,这些挑战使OSPO的运营变得复杂。
话题 4:OSPO的运营困境主持人王晔倞(头哥):观察员tison,你认为OSPO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?tison:企业内部的OSPO往往聚焦于战略层面的开源治理,局限于公司内部运作,较为封闭。
对于开发者而言,遵循开源基金会的规则和社群协作模式,是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。
如果企业缺乏与开源社区协同的经验,就难以实现高效开发。
运营方面,企业经常忽视面向开发者的需求,运营人员难以理解如何在开源社区中有效沟通和推广。
此外,企业过于依赖内部团队进行开源问题解答,而非鼓励社区内的自发交流,这削弱了社区的活力。
话题 5:组建OSPO的时机主持人王晔倞(头哥):在什么情况下企业需要考虑建立或组建OSPO?Keith Chan认为,无论企业规模大小,使用开源软件都会带来成本节省,但若不回馈社区,企业将投入大量资源维护代码。
堵俊平则指出,使用和管理开源软件是所有企业面临的问题,建立OSPO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,提升组织效率和文化。
建立OSPO的时机在于企业遇到痛点,如开源软件选择、维护、分叉后的Bug修复、长期规划和Upstream First(上游优先)原则的实施等。
当企业内部不同团队的架构重复出现,形成“烟囱”效应,或开源项目在多个业务单元中广泛应用时,OSPO的存在变得尤为重要。
综上所述,OSPO在企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,通过解决开源相关问题、构建开源战略、优化运营流程和促进社区协作,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价值。
随着开源在各行业中的普及,企业建立或优化OSPO的需求日益增长。
黄峥之后,电商三巨头已全部隐退
有一个故事曾在浙大留学圈传播甚广。
故事的主人公是黄峥。
2002年,黄峥从浙大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,攻读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。
那时候,由于中国学生在美国GRE考试中成绩太好,以至于美国一些学校怀疑GRE考满分的中国学生有问题。
而黄峥可以精确控制自己的GRE成绩,使之保持在既能被美国学校录取、又不会引起怀疑的分数。
这样的人,一般被称为“学神”。
遗憾的是,纵使是“学神”,也难算准时代的风声。
马照跑舞照跳,时代已经不允许有些人当主角了。
激流之下,黄峥退了
3月17日,电商新贵拼多多发生了两件大事。
一是拼多多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。
截至2020年底,拼多多年活跃买家数达7.884亿,成为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电商平台。
同一时期,阿里巴巴年活跃买家数为7.79亿,京东为4.72亿。
辞任后,他持有的1:10投票权也将失效,名下股票三年内锁定不出售。
早在2020年7月,黄峥就卸任了拼多多CEO一职,这一次,连董事长也不当了,他要去:
黄峥此举被外界解读为“退休”,但实际上,黄峥今年才41岁,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。
更重要的是,拼多多诞生还不到6年,正是打攻坚战的时候,远没有到可以自由潇洒的地步。
所谓的退休,更多是一种“退而不休”。
在拼多多的股东名单中,黄峥目前的股份为29.4%,依然是第一大股东。
黄峥的投票权委托拼多多董事会以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,而在目前拼多多6位董事中,基本上都是黄峥最亲密的战友。
此外,在拼多多的股权架构中,还有着同股不同权等多道“保险杠”,这家公司依然姓黄。
所以,退休是不可能退休的, 让黄峥急匆匆隐于幕后的,更可能是汹涌的舆论。
一个成立不到6年的电商平台,不仅早早上市,更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电商平台,黄峥带领下的拼多多确实耀眼。
但拼多多在极速飞奔的同时,问题也如影随形。
刚成立的时候,从下沉市场切入的拼多多,身上一直是“假货”“低端”的标签。
百亿补贴后,又被贴上了“烧钱”“败家”的标签。
如今,更是深陷“员工猝死”“卖盗版书籍”的漩涡之中。
在外部,拼多多宣传“拼得多省得多”;而在内部,拼多多倡导的是“拼得多挣得多”。
这背后,是拼多多近乎畸形的高效。
2021年初,拼多多员工“润肺”的猝死事件引出了拼多多针对员工的一系列违规操作:
一路狂奔的拼多多,一度处在价值观的漩涡中心。
稀释股权、隐退幕后,黄峥一直想从这个漩涡中抽身。
电商三巨头都退了
黄峥的后退,无意中创造了 历史 。
如今的互联网已是商业世界的中流砥柱,中国电商平台也已经坐上国际市场的牌桌,其中的翘楚,便是阿里、京东与拼多多。
而随着黄峥的辞职,这三家公司的创始人,马云、刘强东、黄峥都已退居幕后。
放在全世界,这都是一个奇观。
纵观大洋彼岸的互联网巨头,扎克伯格、贝佐斯等人依旧奋战在一线,丝毫没有退隐的心思。
虽然都是退居幕后,但三个大佬的路径却大有不同。
2019年教师节,55岁的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一职。
马云的一生,跌宕起伏。
他曾三次创业失败,也曾多次经历至暗时刻,但最终带领阿里巴巴走向了成功。
本以为从此潇洒快意,但谁曾想,马云的光彩被定格在2020年10月24日。
那一天,马老师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开炮,当着一众金融高层的面,直言“银行当铺思维”、“中国金融没有系统”,将中国银行业嘲讽了一番。
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,监管部门约谈,蚂蚁IPO暂停,反垄断呼啸而至。
这之后,马云整整“消失”了88天。
以外滩演讲为分界点,马云和他的阿里,遭遇创业以来的最大危机。
而刘强东,在大洋彼岸败走明州。
明尼苏达一声炮响,江湖从此只剩下东哥的传说。
早在2018年,刘强东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:不会在65岁前退休。
没想到反转来得猝不及防,明尼苏达案结案前8小时,刘强东亲自签发了《京东商城组织架构调整的公告》,调整后,多个事业群负责人不再向刘强东汇报,而是向京东集团CMO、京东商城轮值CEO徐雷汇报。
到了2020年,跟刘强东相关的消息只有“卸任”。
在此之前,京东一直与刘强东深度绑定,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京东的二把手是谁。
可以说, 刘强东既是京东的壁垒,也是京东的软肋。
京东最终没能在刘强东的带领下打破BAT的格局,他不再是弄潮儿,他已经退到了岸上。
总结三个巨头的隐退,星球商业评论文章里的一句话非常到位:
男同志一定要管好“三巴”。
膨胀的巨头
回过头来看,过去的20多年,是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机遇之年。
1994年,中科院以及北大、清华率先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,接入了国际互联网。
这一年,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。
这之后,2003年的非典成了互联网发展的契机,2009年移动互联网迎来腾飞,中国互联网从此势不可挡,一批巨头也由此诞生。
以阿里为例,新财富曾做过统计,阿里巴巴从2014年至今年报披露的重大股权投资,金额合计3958亿元。
在一张号称“最全阿里投资概念股”的表格中,与阿里存在股权关联的公司总市值高达4万亿。
以2019年GDP来做对比,这一数据能超越上海和湖南,排在全国第九位。
互联网巨头们的能量,深不可测。
且已经超越了传统单一行业的垄断性大企业,正在向超级巨头演化。
知名博主“兔主席”就曾对互联网巨头做过一个梳理,他提出了三个维度:大企业、互联网、资本。
这三个维度存在叠加效应,如果只有一个维度足够大,就称为1.0效应。
在1.0效应中,华为、网络、瑞幸分别是大企业、互联网、资本的代表。
以此类推,2.0效应指的是两个维度的叠加,3.0效应就是三个维度的叠加。
而如今的互联网巨头,就是3.0的代表: 大企业 互联网 资本。
对照一下,阿里、腾讯、美团等巨头似乎都是如此。
在此前的文章中,笔者也曾提出过一个论断:
如今“看不到边界”的互联网巨头,已经超越了吴晓波提出的四大利益集团(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,无产阶层、有产阶层)的范畴,成为了第五种力量。
在互联网巨头的生态体系中,既交织着有产和无产(劳资关系),又包含着中央和地方(产业与城市),但与此同时,它们似乎又游离在这四大利益集团之外,看不到边界。
这样的趋势让人感到不安。
尾声
仅仅两年前,垄断这个词离人们还很遥远。
互联网巨头们也曾是国人眼里的“希望”。
无论是电商平台购物带来的方便,还是支付方式带来的变革,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它们赢得了 社会 舆论的支持。
但风向骤然变化。
从马云“飘了”,到蚂蚁金服上市搁浅,再到监管高层的一个个重锤,最后落地为三巨头受罚。
在此之前,互联网巨头们用电商搞垮了实体小店,用网约车抢了出租车的饭碗,用外卖流量入口绑架了餐饮店老板,还要用资本补贴下的送菜服务逼死菜市场小摊贩。
到最后,大家发现,那些被挤垮的小老板、小商贩、小生意人……变成了快递员、外卖员、滴滴司机和送菜员。
大家失去了一切,变成了互联网巨头的打工人。
有人甚至说,这就是新时代的圈地运动。
当巨头们开始利用自己的行业垄断地位,“虹吸”金字塔底层民众的财富时,它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。
正如南方周末说的那样——
反垄断不是反对富人,而是反对为富不仁。